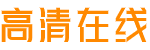在巨大的財務壓力下,商湯為何仍要“all in具身智能”,這究竟是一場深思熟慮的“大棋”,還是又一次無奈的“追風”?
商湯,這家曾經頭頂“AI第一股”光環的企業,近日再次成為業界焦點。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會(WAIC)上,商湯重磅發布了“悟能”具身智能平臺,標志著其在人工智能前沿領域的又一次重大布局。
然而,回顧過去數年,商湯的經營狀況卻不盡如人意,持續虧損、不斷裁員以及主要股東持續減持,讓這家昔日的“AI四小龍”之一深陷困境。在歷經元宇宙、大模型等多個風口的嘗試后,商湯如今又將目光投向具身智能,并為此完成了新一輪25億港元的配售融資。
這一系列舉動,不禁讓人疑問:在巨大的財務壓力下,商湯為何仍要“all in具身智能”,這究竟是一場深思熟慮的“大棋”,還是又一次無奈的“追風”?
1 巨頭競逐,商湯何以躬身入局具身智能?
具身智能,被視為人工智能的下一個“殺手級應用”。它旨在讓AI技術不再僅僅停留在云端進行“思考”,而是能夠通過機器人等物理實體實現對真實世界的“感知-理解-決策-執行”閉環交互。
2025年,具身智能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迅速點燃了資本市場的熱情,僅上半年國內該領域融資便超過200億元,相關融資事件高達130起,遠超2024年全年總和。行業普遍預測,具身智能機器人未來有望形成一個不亞于手機的新終端市場,數量可能達到百億甚至千億級別。
在此背景下,商湯攜“悟能”具身智能平臺高調入局。該平臺以商湯具身世界模型為核心引擎,依托商湯大裝置提供端側和云側算力支持,旨在為機器人、智能設備提供強大的感知、視覺導航及多模態交互能力,推動智能終端向更高層次的自主化與智能化演進。
據悉,“悟能”平臺的核心班底匯聚了商湯聯合創始人王曉剛、前京東探索研究院院長陶大程等視覺技術與機器人領域的頂尖人才。在WAIC現場,商湯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徐立展示了搭載具身世界引擎的人形機器人,展現了其在多視角視頻生成、構建4D真實世界以及自主進行位姿、動作骨架和指令生成等方面的強大能力。商湯還積極與宇樹科技、歸墟機器人、傅利葉等具身智能公司展開深度合作,共同開發“具身智能大腦”和情感陪伴機器人等產品,加速技術落地。
然而,商湯科技的入局并非一蹴而就,其戰略調整之路可謂曲折。
作為曾經的計算機視覺巨頭,商湯在安防、智慧城市等領域一度風光無兩。但進入大模型時代后,以語言模型為核心的AI浪潮席卷而來,商湯等“AI四小龍”因其技術主線仍集中在計算機視覺領域,核心收入依賴政府項目,普遍遭遇發展瓶頸。
商湯在2023年和2024年兩次進行業務重組,從最初的四大業務(智慧商業、智慧城市、智慧生活、智能汽車)調整為“生成式AI、傳統AI和智能汽車”,再到“生成式AI、智能汽車和視覺AI”,直至最新推出的“1+X”架構——“1”代表生成式AI與視覺AI核心業務,“X”則代表智能汽車、家庭機器人等可獨立融資的生態企業矩陣。
一系列的戰略變動,在外界看來似乎帶著些許“追風口”的意味。從元宇宙到生成式AI,再到如今的具身智能,商湯始終試圖站在風口浪尖。
但從另一個角度審視,商湯的具身智能布局或許更像是一盤蓄謀已久的“大棋”。商湯自身在計算機視覺領域多年的深厚積累、在多模態大模型方面的先發布局(如“日日新”大模型體系和SenseCore AI大裝置)、以及在智能駕駛(“絕影開悟”系統)中構建“世界模型”的經驗,都為具身智能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基因。具身智能本質上是將商湯“看懂世界”的視覺霸權,進一步延伸到“改造世界”的終極目標。
在當前AI行業競爭白熱化、自身財務壓力巨大的背景下,具身智能被視為AI技術“落地化”的關鍵突破口,是商湯尋求新增長曲線、實現“絕地反擊”的背水一戰。這種“躬身入局”,既是其技術基因的自然延伸,也是生存壓力的必然選擇。
2 虧損泥潭難自拔,商湯落寞與求變
自2014年成立至今,商湯已走過十余年光景,然而盈利的曙光卻遲遲未現。根據最新披露的2024年年報數據,商湯全年營收37.7億元,同比增長10.8%,但凈虧損仍高達43.07億元,盡管同比收窄33.7%,卻已是連續第七年虧損,累計虧損額超過546億元。這一數字,甚至遠超其7年間累計實現的營收總額(240.13億元),凸顯了其巨大的財務壓力。
持續高研發投入是商湯虧損的重要原因。2024年,商湯研發費用達41.32億元,同比增長19.2%。從2018年至2024年,其累計投入研發204.45億元。盡管商湯將虧損收窄歸因于“資源聚焦與效率優化戰略”,通過削減銷售費用和行政開支來“降本增效”,但這背后卻是不斷進行的裁員。
截至2024年底,商湯總雇員為3756名,較2021年上市時減少了近2500人,四年累計優化人才2357人。坐實的裁員數字,印證了市場中不斷流傳的“裁員”傳聞,不少有實力的技術人才因外部待遇更好而選擇離開,也讓商湯面臨人才不斷流失的挑戰。
二級市場上,商湯股價表現同樣令人擔憂。2021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時,商湯曾創下全球AI領域最大IPO紀錄,市值一度超過1400億港元,隨后更是觸及3500億港元高點。然而,伴隨持續虧損、業務轉型以及靈魂人物湯曉鷗教授的逝世,商湯的投資者們如阿里巴巴、軟銀等紛紛失去耐心,持續拋售股份。截至2025年7月31日收盤,商湯股價報1.60港元/股,總市值僅為592.12億港元,較巔峰期跌去大半,最低時甚至跌至0.58港元/股,不及巔峰時的零頭。
商湯的落寞并非個例,曾經并稱為“AI四小龍”的曠視、云從、依圖在大模型時代也普遍遭遇重創。這批以計算機視覺技術起家的AI企業,在語言大模型浪潮下,其核心收入仍高度依賴安防、交通等政府項目,商業化效率低下,難以擺脫對前期高資本投入的燒錢局面。
為了扭轉困局,商湯在業務上不斷調整。2023年,其業務重心明確轉向生成式AI,并將其收入單獨列出。2024年,生成式AI業務收入飆升至24.04億元,同比增長103.1%,占營收比重達到63.7%,成為其第一大收入來源,也是商湯歷史上增長最快的業務板塊。然而,盡管生成式AI業務狂飆突進,但在一些市場研究機構(如IDC)的報告中,商湯在國內大模型市場的份額卻出現下降,這表明其增速可能并未跑贏整體市場和競爭對手。
此外,商湯在AI芯片領域的布局也面臨挑戰。為了緩解財務壓力,商湯將AI芯片業務獨立拆分成立曦望公司,并由聯合創始人徐冰親自負責。雖然曦望獲得了近10億元的融資,但其財務數據顯示仍處于虧損狀態,且收入水平較低,未來面臨巨大的市場競爭和技術研發不確定性。AI芯片領域“燒錢快、賺錢難”,且華為、寒武紀、小米等國內巨頭以及英偉達、AMD等國際巨頭早已深耕多年,商湯要在其中突圍,難度可想而知。
在高負債(2025年一季度資產負債率高達82.5%)、持續虧損以及大股東拋售的背景下,商湯能否通過具身智能這一新賽道實現盈利,并補齊技術短板、重塑競爭格局,將是其未來面臨的嚴峻考驗。留給商湯試錯的時間,已經不多了。